資產階級時代的「民族」消失
[兩岸史話] 資產階級時代的「民族」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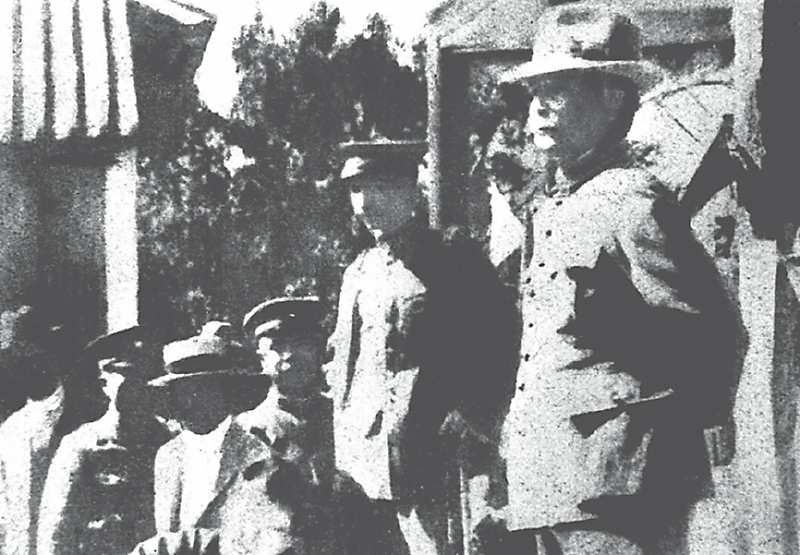
以一種比喻的方式來說,這是一種不僅突破了「地心說」,也突破了「日心說」,甚至突破了「宇宙中心說」的時空敘事,任何以其他模式生成的歷史目的,都會被它消解掉。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開了想像力的空間,對於世界秩序擁有超級的思考格局。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政治空間,則塑造了一種可被時間所克服的空間結構。民族國家式的縱向割裂的空間結構,在共產主義看來不過是一種階級統治的工具,政治的意義不在於對這種階級統治工具的認同,而在於通過階級鬥爭,完成終極的普遍解放;階級是通過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獲得定義,這種識別標準與血統、信仰、種族等等都沒有關係,從而政治的空間結構就基於貧富關係而變成一種橫向割裂的格局。
它打碎了縱向的政治空間內部的統一性,同時擊穿了諸縱向空間彼此之間的分隔物(民族意識),通過橫向空間的分隔物(階級意識),識別出自己的敵人。敵人一方面是在國家內部(本國的統治階級),一方面也在國家外部(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但所謂外部敵人並不是其他國家,因為國家概念本身要被階級概念擊穿,各國的無產階級因共同的階級身分而成為天然的戰友,各種統治階級則是無產階級的共同敵人。
階級關係無國界,由此政治秩序也突破了任何國家界限,天然地以全球為單位,是無產階級國際(international)對(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國際的)資產階級的普遍戰鬥。鬥爭的終結是一個偉大的終極歷史時刻的到來,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超越。這將使得資產階級時代的「民族」(nation)消失,或者說縱向劃分的政治空間消失;由於從此進入無階級社會,橫向政治空間也將因此消失,整個人類世界進入一種普遍均質的狀態。這便是用時間克服了空間。
從另一角度來說,在這一終極歷史時刻尚未到來之前,縱向的政治空間仍然存在,在已有國家的地方,表現為資產階級所主導的階級統治,在還沒有國家的地方,表現為資產階級所主導的民族自決;而橫向的政治空間也一直存在,表現為普遍的階級鬥爭,並作為歷史演進的動力機制。一旦有了對於這樣一種終極歷史時刻的理解,有了對於歷史規律的把握,人們便可以通過主觀能動的行為來推動時間對空間的克服加速到來,這便是無產階級革命。至於這一終極歷史時刻何時到來,在哪裡到來,在不同的地方分別以什麼節奏到來,則有賴於革命領導者的判斷。
這帶來一個衍生結果,就是革命領導者可以基於其判斷,而以各種方式來利用不同的政治空間結構,對給定空間結構進行各種擊穿,又創建必需的新的空間結構,由此而浮現出可以打交道的不同政治對象,可以視情況所需變換政治結盟關係,並能對此進行邏輯自洽的正當性辯護,形成具有極大的政治彈性與靈活性的政策方案。而用以為縱向空間的國家政治進行正當性辯護的各種觀念系統,在橫向空間的階級政治當中是否仍然具有正當性,則取決於革命領導者對於歷史時刻的判斷,但即便仍然有正當性,也是一種工具性的正當性。階級政治有自己的一套正當性觀念系統,它超越於舊有的觀念系統之上,統領並視情況調用各種觀念系統。
在這樣一種時間─空間結構下,一切空間性的東西都被相對化,非終極的、日常時間性的東西也被相對化,它們都不具有絕對的價值和不可通約的差異,它們都將被那個終極歷史時刻所超越,它們的意義也都通過那個終極歷史時刻而獲得識別。在終極歷史時刻的觀照下,一種終極命運審判式的精神結構建立起來,一切日常的禁忌都被打破,一切現實當中的魅惑(enchantment)都被祛除,一種無比宏大的世界觀念被建構起來。以一種比喻的方式來說,這是一種不僅突破了「地心說」,也突破了「日心說」,甚至突破了「宇宙中心說」的時空敘事,任何以其他模式生成的歷史目的,都會被它消解掉。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開了想像力的空間,對於世界秩序擁有超級的思考格局。
但超級格局還對應著另外一重面相。所有的這些超級格局,都以終極歷史時刻來正當化自身,終極歷史時刻在本質上類似於一種信仰。古典帝國也有其終極時刻,由宗教給出,將實現於彼岸世界;對該終極時刻的教義解說,會被轉化為一種法理化的討論,其在日常時間─日常政治中轉化出一種具有可預期性的法權秩序。共產主義的終極時刻基於對歷史規律的理性把握,將實現於此岸世界,對它的解說倘若被法理化,便與此岸世界的資產階級法權難以區分,所以它會拒絕法理化的努力;這就讓日常時間─日常政治本身的可預期性遭遇到困境,一種穩定的日常法律秩序難以建立起來。這樣一種複雜糾結的狀態,必須通過革命領導者的臨機決斷而獲得突破;於是,革命領導者就會轉為共產主義革命的肉身化呈現。共產主義革命歷史當中的一系列複雜難解的困境,也隱藏在這一重面相中。
在這種超級格局下,中國共產黨獲得遠大於中國國民黨的動員效率。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基於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而獲得了新的軍事動員效率,但是此種組織原則與其道德原則並不足夠匹配;更準確地說,國民黨試圖用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但三民主義是一種政治性的理念,而非倫理性的理念,只能為政權進行正當性辯護,並不能起到規範世道人心的作用。於是,強大的組織原則便會喧賓奪主,置換掉道德原則對於組織目標的定義能力。北伐的過程中便發生了一系列過激行動,對傳統社會秩序與倫理形成巨大的衝擊,也令組織目標本身陷入混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