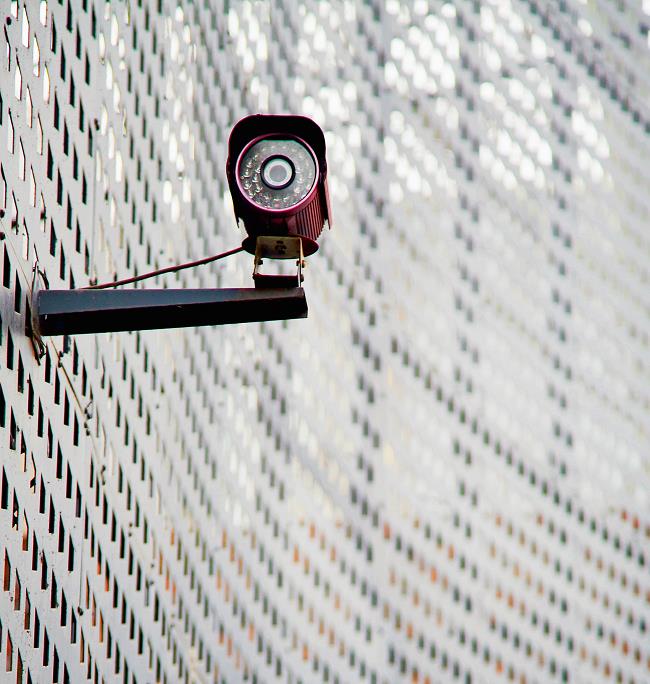海量的攝影鏡頭、雲端更新的大數據以及強大的人工智慧─然後這稱之為「天網」的恢恢之眼,再與記錄民眾一切社會活動並評分的「社會信用制度」整合起來,於是社會中每個個體的狀態都能即時加以掌握:不只是過去的生活軌跡,還包括當下的所作所為,甚至是未來任何可能的行動,都無所遁形。
科幻想像已然成真
這不是科幻小說,儘管已有許多科幻小說描述過這種科技的概念。基本上來說,是將幾種現有已成熟的科技結合起來使用;但要有同時具備物量、資訊量,以及科技品質的國家,才能將概念付諸實行—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天網之下,密而不漏,在公共管理層面該是多好的概念。既能夠實際提升追蹤通緝犯的效率,增加大小刑案的破案率,而且密不透風的攝影鏡頭本身就具備一種嚇阻能力,更別說天網系統一旦打出名號,那麼這種高科技對於潛在的犯罪者的心理壓力有多重了。但是就如同硬幣有兩面,萬事萬物也一樣。天網之眼所映照出來的,不只犯罪者,而是所有良善百姓在內。民眾不管是出門遛狗、購買泡麵、蹺班散心,全都會曝光在雲端上的無形之眼裏。這就帶出爭議:公共的管理、隱私的人權,究竟孰輕孰重?
剝奪人性的完美管理
假如一個推行公共管理的政府能夠公正公平、完全的理性思維、一切都以追求公共利益為優先—那麼個人的人權隱私在國家大義面前似乎真的無足輕重。可是,不管再怎麼管理,當人被看作必須仔細「管理」的物件,就是把「人」降格為「物」,只求服從和統一標準,如同剪刀只需被握持剪開布匹。
因此任何的信用制度、乃至任何的評分系統,其實都是情節輕重不一的「物化」:捨棄掉一個人多餘的特質,只用特定的標準來評價。人之所以為人的各種面向(人格、記憶、情感等)自此不再得見,僅是一個或一組數字—最好的管理,本就是剝奪人性的。
物化的天賦人權
因此為了區別人與物的差別,哲學家才提出「天賦人權」:人生而為人,稟賦著不可轉讓、放棄、受害的權利。只有在個人為了增進或保障自身更高權力的情況下,才會提供部分權利以組成政府,足以調度更多力量來行動。亦即,政府就是「將人民交出的權力逕行行使」的集合體,例如人民交出了「行使武力」的權力給予政府組成軍、警等武力組織,又交出了「收集財富」的權力給予政府組成稅捐單位……
單就理論而言,當每個個人交出支配周圍觸手所及的一切權力給政府時,政府就將能擁有足以解決人民一切問題的能力。不只是金錢、槍枝等有形之物,還有像法律、教條等行為規範,以及終極的權力—「生殺予奪」,包括處置生命、健康、記憶、印象等「人生而為人」的象徵。可是,若極端到為民眾的生存管理而控制民眾的一切自由,看似是以一項權利換取另一項,正當公平;但在這裏卻無法成立。
集體優先的困境
單一個個體是弱小的,因此個體會組成群體,群體產生出中樞,能夠統轄並調動每個個體,去解決單一個體因弱小而力有未逮之處。但是凡事總有先後順序,因此總是必須有所取捨:在理性的思維之下,顯然力量較強的個體需要全體群體支援的優先度是更高的,因它們對群體產生的貢獻度更高。這是一個困局:群體力量最終只會為特定強者而服務,因為它們就代表了群體。
中國大陸古代就觀察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個人為群體盡瘁,群體為個人鞠躬」的想像,最終還是會通往邏輯的陷阱:你為人人,人人自然不必為你。因為若個體將觸手可及的一切權利一點不剩地交了出去,實際上這個個體本身也就成了空殼,當天網能夠「看」見一個人的一舉一動時、當信用系統能夠記錄並決定了一個人的一生軌跡時,這個人作為「人」的獨立性也將變得模糊:在天網視線下的行動,將很難稱作是出自於自身的意志;而由社會信用系統決定「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的判斷,在事實上否定人的自主性。交出隱私的意思,其實等同於交出做決定的權利。現代立憲國家多在憲法中追認天賦人權,也正因如此,在現代法治意義下,政府的權力不能「去到盡」,民眾也無法將此身一切權利都讓與政府。
沒有簡單的答案
「個人人權」與「公共管理」兩者本是衝突,當管理一方為求全體的良善管理之必要,而越過原有界線從個人處拿取了更多的權利時,這便成為「必要之惡」。但這必要之惡本在談論「必要之事中的邪惡面向」,重點在惡,而非「必要」。這本是為了反省在立身處世時,那些被有意無意帶過的錯誤惡行,而非行惡的理由。
要實現公共管理,就必須要有得自公共的力量,但在這個管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將會導致被管理個體的物化,並進一步失去了各項權利,最終僅僅成為組成社會的一個部件,而非獨立的人格。如同組成人體的其中一個細胞,不能稱作人一樣。只是,一顆良善的大腦,也確實能夠整合並發揮出身體各處最大潛力,進而爭取整體身體的存續和發展。
人類百十萬年來的進化路線就是如此。公共管理對於促進社會進步仍舊是不可或缺的,只是,若不能時時留意人權隱私的界線,也可能會在意想不到之處付出代價。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