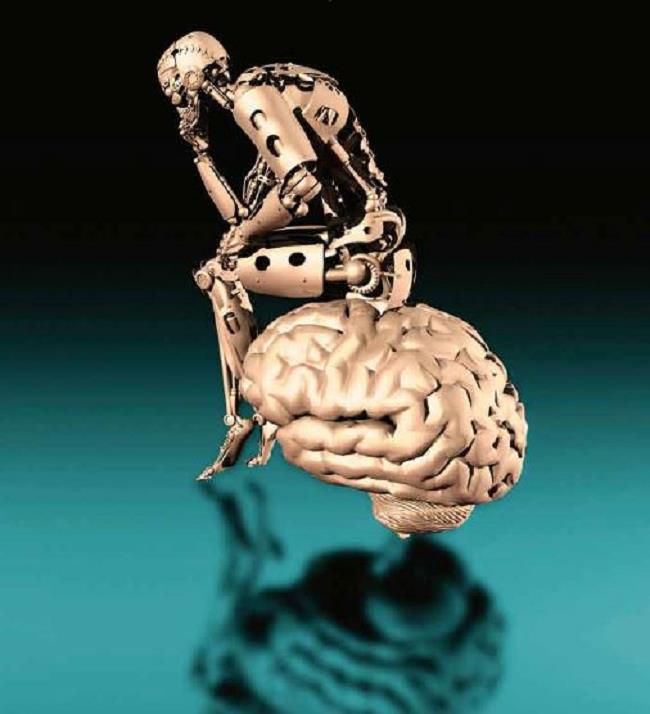自由是當代的主題詞之一,我們經常談論它,並認為比以往時代的人們更多地擁有它。但這也許只是一種美好的幻覺。想想以下這些你熟悉的場景:使用各類App在網上導航、約車、叫外賣或與親人朋友聊天,當你認為自己輕鬆地運用技術掌控生活的時候,其實有多少決定是真的由你自己所做?你喜歡什麼、打算做什麼、與哪些朋友更親密,這些問題都因技術的介入而發生改變。而更大的隱患則在於,我們對於時刻暴露在網路數據流這件事情往往缺乏自覺,而「技術」則透過它們,能比我們還更瞭解我們自己。
科學技術的進步,是一般人喜聞樂見的話題,但這裏要講的是另一個故事。雖然人們從技術普及中受益,但同時,我們也可能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價。在上述這些場景中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對生活的自主權,正不知不覺地被技術壟斷了。
文化臣服於技術
技術具有辯證性,這並非新近的發現。柏拉圖(Plato)的《斐德羅篇》(Phaedrus)中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與友人特烏斯(Theuth)神的爭論,是關於這一話題早期的經典文獻之一。特烏斯發明了文字,並高興地認為這項文明有助於增強記憶和智慧;而塔姆斯則提醒他,文字可能包含反面的功能:它使人對文字符號產生依賴,從而忽略事物本身,有可能使人們記憶力衰退,並把掌握資訊誤以為擁有智慧。
這段關於技術利弊的討論,被傳播學者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置於《科技奴隸》(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一書的開篇。波斯曼是國際知名的傳播學者、文化批評家,也是「媒介生態」概念的提出者。媒介生態學關注技術,尤其是媒介技術發展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並由此闡發以技術為核心的媒介環境,如何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和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
按照技術與社會、文化系統的關係,波斯曼將人類技術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依次是: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在最早使用工具的文化中,工具並不會妨礙人們相信既有的傳統,而是信仰在引導工具的發明和限制其使用。但進入技術統治階段,工具開始改變社會物質結構,並在思想層面打下烙印,為自身的發展而要求傳統觀念臣服,工具和文化開始交戰。但直到傳統社會和信仰體系被完全破壞,工具和文化的依存關係被顛覆,控制權發生轉移時,技術壟斷時代才真正到來。
自1990年代起,美國已進入技術壟斷時期,之後,更多的國家步入這個行列。技術壟斷,可以理解為我們的生活和世界被技術極權主義所統治。波斯曼在書中表示:「技術壟斷是文化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思想的存在方式,技術被神化,文化要在技術中尋求認可和滿足,並且聽命於技術。」這意味著文化生活必須要尋求技術的認可,而且在技術的侵蝕中一步步讓出自己的領地,在此階段,技術和人的關係完全顛倒,人類可能淪為技術的奴隸。
科學至上 壓抑人性
技術是如何實現社會控制,並佔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波斯曼認為,這個過程開始於19世紀早期,隨著科學發現和實證哲學迅速發展,技術不斷為人類提供便利,拓展人們的認識,成為進步、富裕和文明的象徵。當人們接受新技術的同時,也接受了它背後的整套價值觀,舊的習俗和信仰被逐漸拋諸腦後。波斯曼列舉了很多例子,如青黴素代替了禱告、電視代替了閱讀、娛樂代替了思考……它們發生在不同階段和不同的社會領域,但其影響無疑越來越廣泛和深入。
技術壟斷時代營造了一種假象,即科學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檢驗標準,那些無法被量化和證實的感觀和信仰,都被判為「可疑」。要理解這一點並不困難,我們這個時代就存在著諸多有關技術的迷思。比如在對人工智慧的流行觀念中,演算法和演算速度決定了認知的科學性,很多人將這種認知模式視為「客觀」,並認為其智慧水平遠超乎人類,因而更可信。又如在傳媒業,尤其是所謂新媒體行業,根據演算法而獲得最大化的流量,越來越成為決定資訊品質量的標準;相反,傳統的採編人員正逐漸喪失對真實性和重要性的話語權。
在技術壟斷時代,最終價值的判斷標準外在於人類自身,一切都由技術決定,造成了價值判斷與行為的剝離。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行為通常服務於一個更高的目標,這個目標則隱藏在高度技術化的帷幕之後。它的技術性以及神秘感,使其很容易被某一部分人所操縱,而多數人則盲目地被驅使。甚至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述「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時所指出的,許多人就像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樣,從事著高度技術化的工作,對每一個程序背後服務的對象喪失了敏感,最終就可能脫離人類道德的軌跡。
如何逃離或反抗
波斯曼的目的不是危言聳聽,他只是指出,技術與人性的矛盾,在技術壟斷時代將不斷激化,並左右人類文明的走向。在他呼籲關注技術壟斷近30年後,我們面臨的處境更加危險。資訊技術、生物工程、航天和醫療,這些領域技術的飛速成長正形成越來越強大的統治力量,而谷歌、臉書、蘋果和亞馬遜等科技公司,也成為新的技術代言人。
但同時,人們對技術的威脅也會看得越來越清晰。比如去年發生的基因改造嬰兒事件,就引發了技術與倫理邊界的激烈討論,呼籲對技術加強監管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不斷爆發的關於「假新聞」、「後真相時代」的爭議,所反思的正是「技術如何重新定義事實」的問題。此外,由於頻繁陷入資訊操控、侵犯隱私、阻礙競爭、威脅民主等爭議,曾經身為偶像的科技公司們,也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甚至要求拆分它們以打破技術壟斷的建議也被正式提出。據《紐約時報》還報導,一些上流人士正想方設法脫離技術的控制,減少網路設備的使用,讓人際交往的價值被重新重視。
但人們可以逃離技術的掌控嗎?覺醒的一部分人又能做什麼?對此,波斯曼承認自己沒有很好的建議,但他特別強調,他並不是反對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像工業革命時期砸毀機器以反抗剝削的盧德運動(Luddite)若放在當代,基本是徒勞的。我們應該尋求與技術體系達成新的和解,建立人和技術之間更加平衡的關係。
而主要的途徑是改變教育,透過控制這一社會資訊系統的核心,重建人們對於技術和文明關係的認識,抹除當代人由於短視而賦予技術的奪目光環。技術壟斷有相當的迷惑性,以致於很少人意識到技術的神話是以壓倒人性為基礎的;更悲觀地講,即使意識到這種對立,人類在面對技術帶來的利弊時,也難以取捨。而教育能夠對這些問題重新發問,在思辨中培養人類文明「忠誠的抗爭鬥士」。今天重看波斯曼的這一呼籲,似乎仍然充滿遠見。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4期